李公明︱一周书记:历史风雨中的流亡者及其……知识共和国
- 财经
- 2025-04-10 12:17:04
-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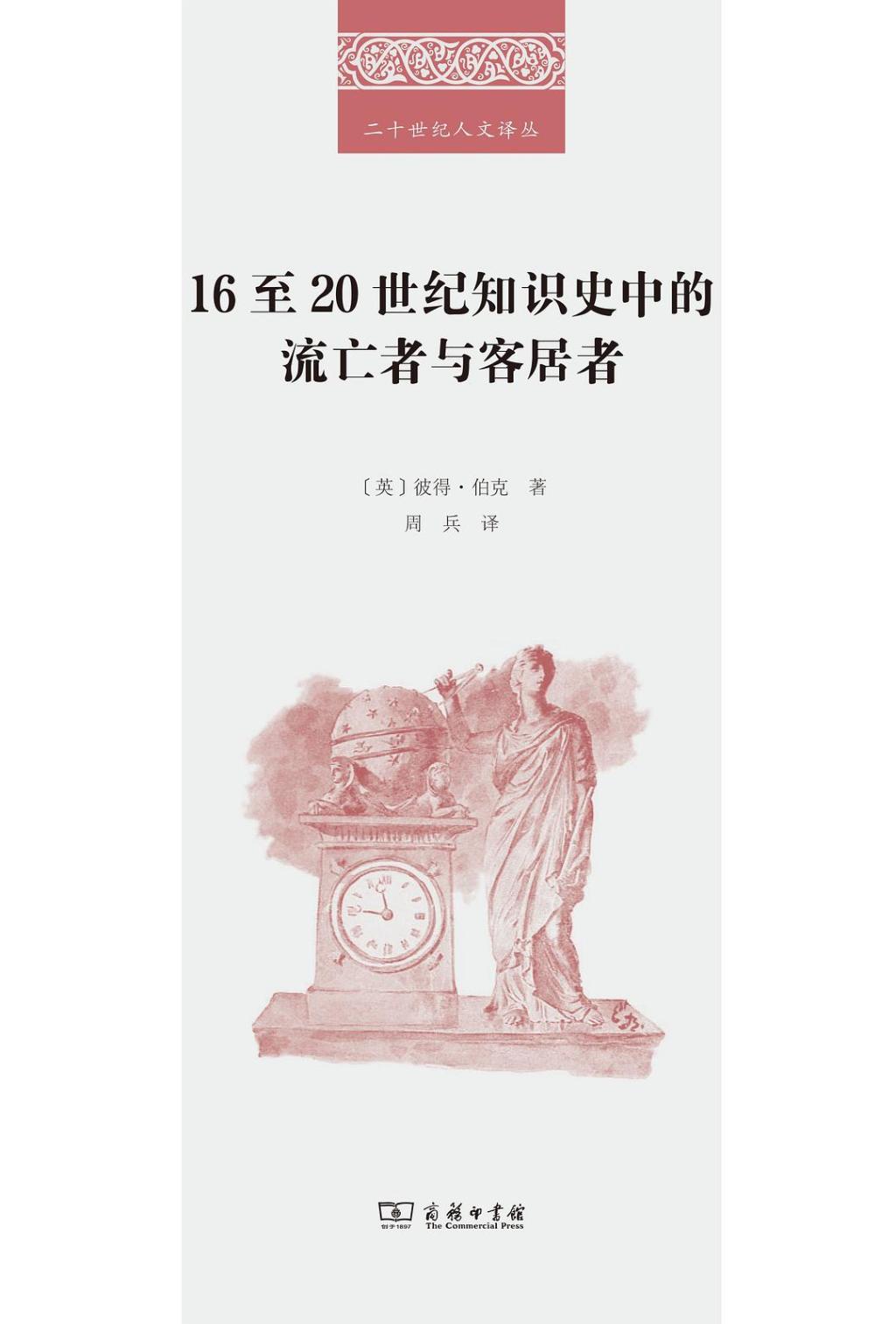
《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英] 彼得·伯克著,周兵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3月版,2025年3月版,297页,88.00元
昨天读一篇题为《特朗普正在把美国科学家推向欧洲的怀抱》的文章(原刊于2025年3月27日《经济学人》),文章说约翰·冯·诺依曼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是逃离纳粹德国、奔赴美国的一批杰出科学家代表,并由此开创了许多全新的研究领域,对美国科学创新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今天,由于特朗普政府削减科研经费,并出于政治原因打压气候科学家等研究人员,因此欧盟十三个成员国的科技部长在3月20日联名致函欧盟委员会,呼吁“立即行动”,使欧洲对那些“可能因研究遭到干涉、遭遇动机不纯且粗暴的资金削减的杰出海外人才”更具吸引力。一位官员也表示,欧洲研究委员会(ERC)将提升对资深科学家的资助力度。德国的马普学会称,已有多位美国顶尖科学家表达了迁往德国的兴趣,机构正在评估应对方案。应该说,无论接下来的情势会如何发展,欧盟科技官员的反应是有远见的。
正在这时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Exiles and Expatriates in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1500-2000,2017;周兵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3月),真是感慨于历史风云的翻覆竟然如此令人猝不及防。眼看着二十一世纪知识史上又要出现一批新的“流亡者”与“客居者”,而且这次是从美国、从自由女神的脚下流向四方,知识史上一个新的严重时刻或许就这样降临了。不过正如彼得·伯克在书中所论述的,流亡者和客居者为知识生产的全球化、去地方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就不必那么悲观。该书最后附了一篇题为《论英国脱欧》的文章,是作者在2016年该书完成之后面对英国即将脱欧而写的。伯克指出,脱欧是为了限制移民的数量,而这对英国的经济和文化都将是一场灾难。因为“如果移民的源流枯竭,或者只是严重减少了,在认知多样性(cognitive diversity)方面造成的损失,其后果也许假以时日才能完全显现出来,但它们很可能就会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英国把自己同其他的观点隔绝开来,就将使英国,人变得越来越封闭,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缺乏创造力。本书中所讨论的案例表明,即使没有人真正想要这样的未来,但是假如英国脱离了欧盟,它将在几十年后不可避免地出现”(194页)。这番话看来也可以用于分析今天正发生在美国的事情,一个“越来越狭隘、越来越缺乏创造力”的美国,难道是那里的选民们希望看到的吗?
该书的“译者序”中谈到伯克论著和史学思想的翻译引进、学习借鉴,堪称新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中的“彼得·伯克现象”,借用伯克的知识史系列著作里的观点,这一现象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分析当代史学跨区域、跨文化传播与接受的知识史研究案例(3页)。的确是这样,我在近两年给研究生讲历史图像学方法论的时候,也谈到了系统地研读彼得·伯克相关著作的重要性。对于我们的艺术史研究来说,伯克对于图像研究的重视和研究方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可以看作是伯克的《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2000;陈志宏、王婉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和《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the Encyclopedie to Wikipedia,2012;汪一帆、赵博囡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的专题性续编。在《知识社会史(上卷)》的“导论”中就已经谈到波兰社会学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zniecki)移民美国和俄国学者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流亡巴黎后对知识社会学的复兴做出的贡献,也谈到了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学者常把自己看作“文人共和国”(Respublica litteraria),“这一说法表达了他们超越国界的群体归属感”(《知识社会史(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21页),同时还强调了知识生产的社会情境问题。在第四章“知识之定位:中心及其边缘地带”中对知识生产的旅行与传播更有全球语境的论述。因此,从这些议题延伸到对于流亡者和客居者移民语境中的知识史的关注是必然的。在“导论”中谈到“把图片(包括地图)看作知识的交流途径并用插图的方式来避免逻各斯中心论(logocentrism)”(同上,14页) ,有点遗憾的是,在现在这部《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中却没有了图片与地图。
从伯克关于知识史的个人研究语境来说,对于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这个特殊专题的研究显然是以知识史、社会史与流亡史、移民史以及国际政治史相融合的方法来进行的。与《知识社会史》的研究“集中于知识的结构和发展趋势上,而不是关注单纯的个体”(同上,前言于致谢,i)有所不同的是,以“流亡者”和“客居者”作为核心对象,使研究焦点主要落在作为知识生产者的个体身上。通过对个体际遇、研究贡献的分析而切入知识生产的发明、接受和传播的动态过程,在多种层面上解释学者个人与所在地在知识生产领域中发生的互动现象及其文化价值。从目前流行的全球史研究视野来看,伯克关于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的研究恰好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知识话语与“去地方性”文化融合的重要视域。
德洛尔·瓦尔曼(Dror Wahrman)在该书“前言”中谈到“如何来看待作为历史学家的彼得·伯克呢?”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点困难,因为几乎没有彼得未曾研究过的话题。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彼得·伯克的博学和在多个史学领域取得的成就的确令人敬佩。瓦尔曼举出伯克的三本重要著作来代表他的三个重要研究方向:《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1978)的精英与大众文化研究、《对话的艺术》(The Art of Conversation,1993)和《欧洲近代早期的语言和共同体》(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004)的语言的社会史研究以及《制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1992),其中谈到《制造路易十四》“重塑了我们对于欧洲专制君主制度全盛时代的理解,把路易十四作为第一个近代传媒的现象来研究,而国王本人被视为一个媒体大王,他再一次地早早地引领了这一种研究类型的风气”。另外还顺带提到《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的众多语种译本,说明“就文化和语言的影响范围而言,当代历史学家中几乎无人能够望其项背”(3页)。就这部《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而言,我觉得瓦尔曼在“前言”一开头说的那则逸事是颇有意思的:当伯克离开任教的苏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前往剑桥大学面试的时候,一位面试官问他:伯克博士,你会说哪些语言?”他回答说:“嗯,我懂并且在研究中用到了从莫斯科到里斯本之间的各国语言,不过我的挪威语口语不是很好。”最后他被聘用了(1页)。我想到的是,对于像全球史和知识史中的流亡者、移民者这样的研究课题来说,语言能力的要求特别突出,其挑战性远远大于当年那些流亡者来到一个新的国度所面临的语言问题。
如果就研究者个人语境来说,彼得·伯克的个人身世和经历也为他的知识史中的流亡者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个人体验。他的祖父母是从爱尔兰西部来到英格兰北部的客居者,而外祖父母则是由于担心种族清洗而逃离俄国的流亡者,家族的历史自然使家庭生活中也具有了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氛围。后来他在老师和学界同仁中认识了许多流亡者和客居者,与有些学者有着多年的交流讨论,其中也有我们在阅读中比较熟悉的学者,如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人。在他举出的名单中,可以看到他与这些流亡者学人的交往明显具有跨学科的特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学术研究特征。
伯克在“导论”中首先阐明本书是知识史和移民离散史这两种研究趋势的交集,“涉及流亡者和客居者,以及可称为‘流散的’‘移植的’或‘转译的’知识。……本书还可以被描述为一篇社会史、历史社会学或历史人类学范畴的论文,受到了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米歇尔 ·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人著作的启发。曼海姆曾经两度流亡,先是从匈牙利到德国,再从德国转至英国,他认为知识是社会性存在的。此论原意本是泛指,但对于流亡者们却尤为适用,因为他们必须应对生活处境所发生的重大变化”(10页)。对于我们来说,也必须认识和反思我们的知识也是“社会性存在的”,无论对于学界中的功成名就者还是精神上的流亡者也同样适用。
究竟什么是“流亡”和“流亡者”?作者从欧洲多种语言的词源和历史语境中做了解读,他认为作为流亡者的西班牙哲学家何塞·高斯(José Gaos)自创的新词 transtierro(移植)很有价值,带有双向的相遇和变化之意。另外也谈到了“难民”(refugees)和 “客居者”(expatriates)的词源和词意变化,这些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真实涵义自然有区别,但也并不总是泾渭分明。这让我想起在我们的汉语生活经验中,常用的是“流亡者”和“移民”,“客居者”则很少用;但在实际上使用“流亡者”也是隐含有某种立场和情感倾向,因而也要受到所涉及的人和事件的具体语境制约。因此伯克说“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拉丁美洲知识分子既没有被驱逐出境,也未受到严重威胁,而只是因为反对非民主化的国内政权,选择了离开祖国。在存疑的个案中,我会用中性的名词“移民”(emigrant,émigré),而在同时讨论到流亡者和客居者的时候,也会如此措辞。”(12页)有时候,“难民”或“流亡者”的标签令人不愿意接受,比如智利作家阿里尔·多夫曼(Ariel Dorfman)和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都是这样。值得注意和区分的是,流亡者基本上是不能回母国的,生离死别的痛苦一直伴随着他们;客居者通常可以来来往往,但是常常会把自己的际遇与留在母国的亲友熟人相比较,总有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态。无论是流亡者还是移民,都会遇到精神上和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如事业的中辍、不安全感、孤独和乡愁,以及失业、贫困、语言不通、与他人的冲突等等。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流亡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创伤,有时甚至会导致自杀。总之,就如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结束流亡美国的生涯后讲的一句话:“每一个移民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是伤痕累累的(beschädigt)。”伯克接着说,“不论是在思想还是情感上,流亡者都出现了脱位。”(15页)
容易被一般人所忽视的是另一种流亡者,用伯克的话来说就是“内部的流亡者”:“许多人因反对当权的政治或宗教制度,虽然人未离境,但却过着像流亡海外一样自我放逐的生活。在近代早期欧洲,有无数类似的例子……在20世纪,类似的持不同政见者范围更广,如犹太人语言学家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他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得以幸存偷生,将自己真实的思想倾诉在日记里;再如俄罗斯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他因参与人权运动而受到内部流放,从莫斯科被驱逐到了高尔基市(Gorky)。”(19页)这类流亡者也不在伯克这本书的讨论之中,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谓“内部的流亡者”的涵义难以明确界定,个人身份、生存际遇和社会关系等情况差别很大,与思想探索和知识生产的关系更为复杂。想到伯克竟然在国家之间的流亡者与客居者的研究视野中也能关注到“内部的流亡者”的存在,已然很令人感佩。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发表在《南方周末》2006,1,12,李公明专栏“穿越记忆”;后收入个人文集《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三十年集”系列丛书,2011年),谈的议题是“在20世纪的政治思想史上,流亡者的诗歌是否可以占有一个恰当的位置”。我在文章中谈到,其实真实的流亡者身份并没有凝固在空间和护照本上。从1979年起侨居美国的苏联诗人德·博贝舍夫说,“所有人都是流亡者”;波兰流亡作家贡布罗维奇认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名副其实的是流亡者”;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说:“诗人是流浪的犹太人”;学者艾德华·萨依德希望知识分子能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 这些言说都把“流亡者”这个概念放置于思想的空间和心灵的状态中考量。心灵上的流亡、自我放逐是对日常状态中的非流亡状态的揭露与反叛,是进入思想史的必由之途。这也正是伯克所讲的那种“内部的流亡者”。
伯克说了,“黑云也有银镶边,本书着重关注的,是流亡后的一些积极的后果……本书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流亡者和客居者对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在积极的方面自然是功德无量的。但即便如此,流亡造成了事业的中辍,如果没有流亡,他们创作的论著和对知识的贡献可能更多,虽然具体的损失永远无法估算了。”(15-16页)因此,“本书试图揭示的,是不仅在知识传播,而且在知识创造方面,流亡者和客居者们所做出的不同寻常、数量惊人的贡献”(20页)。另外,从知识的创造与传播的视角来看,正如伯克所说的,“事实上,整本书都可以说是一项接受史的研究,其中有两重的意义,既包括寄居国的人们对于流亡者或热情或冷淡的接纳,也指对他们的观念及所带来的知识给予的或积极或创造性的接受”(39页)。在今天的全球史研究中,接受史是所有思想、知识传播研究中的关键一环,其中也必然会受到不同利益立场上的接受史观的影响。
同为流亡者的律师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归纳了流亡者和客居者应对生存的三种文化策略:融入新国家的文化,对其文化加以抵制,而最有效的第三种策略是折中与综合。伯克的研究表明,对于知识的贡献,主要来自那些立身于这两个极端做法之间的学者(17页)。书中所论述的学者个案的确都可以说明,放弃自我与固守自我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不利于学者在新的国度环境中创造新的知识。伯克指出本书中的研究是“集中在一些个案的研究上,将侧重在流亡者们对知识的贡献与创造这些知识的个人和群体所身处的境遇之间的关系上”(20页)。当然他很清醒地看到在这里的个案研究必然会遇到“冰山问题”和“马太效应”,前者指的是被研究者往往只是一个群体中相对较为明显的一角,因此要尽量认识到那些略次一等的学者所做贡献的重要价值,从而免于陷入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所提出的著名的“马太效应”(《新约》:“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即一些不知名的科学家的发现和观点常常被记在了一些著名学者的名下(21-22页)。
更重要的是,伯克认为“这项研究和写作的动因,不仅是罗列流亡者们对知识所做出的各种贡献,而且要探究其根本,是什么使得其贡献卓然不凡?在审看最终‘产品’的同时,也检视生产的‘过程’,试图揭示移民们对知识的各种贡献是如何做到的。这个问题也许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去地方化’(deprovincialization)。更确切地说,流亡者与接纳他们的东道主之间的不期而遇,导致了一场双重的去地方化的进程”(23页)。流亡者与东道主在相互接触、交流中均有可能实现“去地方化”,也就是打破原来固化在地域中的知识生产,获取新的思想方法和新的知识。因此,他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流亡作为一种教育”的观点。也就是说,流亡者与在地民众双方在接触当中都会学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如果流亡者回国之后,其祖国的学生们也会有同样的收获(24页)。最后这一点颇有意思,他由此说到虽然“人才外流”的消极后果显而易见,但有时也有积极的方面——当某些流亡者返回故乡的时候也会带来新的观念与知识,如1945年以后许多还乡的流亡者将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带回了德国(24-25页)。
“流亡作为一种教育”使我想起马克思流亡伦敦三十多年,恩格斯在写给他的一封信里写道,“流亡是一所学校”,但是据说马克思并不怎么喜欢这所学校,他曾经说流亡政治是“一所学习丑闻和平庸的学校”。但是在伯克看来,马克思在英国的生活长达三十四年,经历了伦敦博览会(1851年)、印度“土兵起义”(Mutiny )和反英起义(1857年)、兰开夏“棉荒”(1861-1965年)等事件,“让他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发展进程”(139页)。这也应该说是“流亡作为一种教育”的一种过程。
既然“去地方化”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创造过程,伯克认为在这个“伞式术语”(umbrella term)之下涵盖了多个具体进程,它们是分别是转介调和(mediation)、疏离超然(detachment)和融合会通( hybridization )。这是贯穿全书的三个关键词和基本分析方法,在第一章“来自边缘的视角”中分别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而且在论述中均以不同学科的著名流亡学者为案例,是一份非常精简和难得的另类学术史注解。其中一些观点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有重要的启发性。比如关于“疏离”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因为流亡者与寄居地之间的疏离关系而带来了“全局感”、长时段方法(tongue duree)和冷眼旁观的视角,后者如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讲的“陌生人的客观性”(30页)。另外还有从德国来到美国的历史学家弗里兹·斯特恩(Fritz Stern)所讲的“双焦视野”,意即用美国人的眼睛去看待德国事物,而在看美国的事物时,用的是德国人的眼睛。在今天的知识和信息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无需非要踏上异国才能获得“双焦视野”,问题是我们在知识传播的信息场中能否自觉做到视角转换和“概念位移”。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伯克从流亡者、客居者的学术创造的视角所提出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重要见解,往往是在通常的学术史系谱中容易被忽视或误解的,因此我觉得该书是一个很好的另类学术史研究文本。
第五章“大逃亡”主要论述的是在1789年后,则主要是政治流亡者或种族清洗的受害者。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30-1831年发生在波兰的反抗俄国统治斗争的失败和1848年欧洲“民族之春”的革命先后形成了三次流亡与移民离散的浪潮,但是伯克比较集中论述的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十月革命后离开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案例和三十年代的犹太人大逃亡浪潮。关于俄国革命,他指出一直要到1919年俄国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对者们才开始大规模逃亡,他们最主要的落脚点是柏林、巴黎和布拉格。1922年是离乡潮的关键年份,一百五十多名学者遭到驱逐,其中不少人是乘坐臭名昭著的“哲学船”来到德国的,被驱逐的哲学家包括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等人。
“俄罗斯的损失成为其他国家的收获,其中以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最为明显。”(142页)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亲身经历和异国感受激发起流亡者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原因的探讨。三十年代主要来自德国的犹太人和知识分子流亡者,规模之大和学者比例之高是以前没有过的:“有近1700名德国学者和科学家在希特勒政权初期遭到解职,其中75%以上是犹太人。除了犹太裔学者(在当时,只要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就会被解职)之外,难民中还包括配偶为犹太裔的一些个人,以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汇总起来,超过五分之一的德国大学教师因故被解职。”(155页)关于在这样规模的流亡浪潮中产生的知识创造,伯克认为“在知识层面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无疑就是深具理论积淀的难民与其东道主的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从而以一种17世纪胡格诺派难民所未曾有过的方式制造产生了新的知识。如前所述, 20世纪30 年代的移民物理学家被形容为德国理论和英国实验传统之间的‘架桥者’。这些物理学家就是文化的转译者。”(179页)除了对学者个人案例的研究之外,伯克还特别关注跨学科的研究机构——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馆和社会研究所,它们因其各自在艺术史和社会学领域的贡献而闻名,但其影响绝不局限于这些学科。进而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个机构对其寄居国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强调了来自德国的艺术史和社会学这两个学科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美学术界的重大贡献:由于在当时两个学科的基础更多地植根在中欧而不是英语世界,因此“使得流亡者实现了充分的临界价值,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远超出其人数比重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在英国”(163页)。这一部分也是我在阅读该书的时候收获最大的地方。
在今天看来,后冷战时代新的地缘政治使流亡与移民的问题更为复杂化,但是知识的传播与创造仍然不会中断,在历史风雨中的知识共和国永远屹立不倒。因此,前面所讲的欧盟科技官员的远见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有话要说...